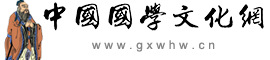栏目: 国学理论 作者:佚名 热度:
编者按
非遗学是一个新学科,一个独立的学科。本文作者冯骥才,是中国非遗保护事业的开创者,更是倡导者和实践者。区区万言,却是他几十年实践与思考的凝练,无疑将为非遗学者和从业者指出前行的方向和方法。本刊将以上下两篇的形式,分两期刊发全文,以飨读者。
非遗学是一个新学科,一个独立的学科。本文试图阐述它无可辩驳的独立性,它的学术本质,从元理论角度勾勒出非遗学卓尔不群的学科样貌。
一个新学科在刚刚确立时,常常会被怀疑它的独立性。新学科的倡导者们必然要遭遇挑战,不时会被诘问:非遗不就是民间文化吗?有必要另设一个学科吗?它本身能否成为一个学科?它具备足够的材料盖一座高楼大厦吗?
若要做出有力的回答还要靠新学科自己。
非遗的缘起
首先要说,非遗学的怀疑者毫无疑问是被历史误导了。
这个历史是在“非遗”诞生的过程中发生的。
20世纪后半期,人类开始认识到前人留下的历史创造中,除去物质性的遗址、建筑、器物、艺术品之外,还有大量精神性的遗产保存在代代相传的口头、活态、无形的行为与技艺中。它们和物质遗存一样,同样是必须永远保存的历史财富。然而人类任何一个伟大的自我认识,最初都是知音寥寥,非常孤寂。这些具有先觉意义的认知,最先只在日本与韩国等一些国家的学者中,直到本世纪初才渐渐得到国际的共识。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类文化遗产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是公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被简称为“非遗”。
历史地说,非遗是一个伟大的概念。它的诞生,表明人类对历史遗产认识的一个新高度,一个新突破,一个新发现;它发现了人类在已知的物质文化遗产之外,还有一宗极其巨大、绚丽多姿、活态的历史遗产,这便使它得到抢救和保护,免于在时代的更迭中泯灭。这是人类一次伟大的文化自觉,是文明史上一个伟大的进步。
早在非遗概念出现之前,人们将这一类型和范畴的文化称为“民间文化”,并建立起相应的科学而完整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譬如民俗学、民艺学、民间文化学等。
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民间文化的生长非常缓慢。它不是发展的模式,而是一种积淀的模式。它一直保持着相当稳定甚至是一种恒定的状态。然而,工业革命以来就不同了,社会骤然转型,固有的民间文化开始瓦解。这一变化在我国来得晚一些,到了20世纪后期,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冲击,民间文化才快速消散和面临濒危,致使一些敏感而先觉的人士与学者急切地呼吁抢救和保护。此时,对民间文化的称呼也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过的改变,比如在“民间文化”后边加上“遗产”二字,称为“民间文化遗产”;再比如本世纪初进行的大规模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于是,这一时期(21世纪初),同时出现两个概念:民间文化遗产和非遗。这两个概念本质相同,不同的是,民间文化遗产的概念来自学界,非遗的概念来自政府,因为非遗是由各国政府共同确定的。
政府作为遗产的第一责任人,为了便于对遗产进行管理,必须将遗产分类。于是文化遗产被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物质性的文化遗产,一种是非物质性的文化遗产,即非遗。可是,非遗是个新概念,需要知识支撑;由于非遗与民间文化在客观上是同一事物、同一范畴,故而,非遗最初使用的知识,都是从现成的民俗学、艺术学去拿。连国家制定非遗名录的分类,也参考了民俗学与艺术学的分类法;甄选和评定国家非遗的标准,也大多来自资深的民俗学者和艺术学者的修养与经验。这样,人们自然以为非遗只是一种政府称呼或官方概念。进而认为,所谓的非遗学不过是政府遗产保护不成体系的工具论而已;非遗学没有完整的知识,最多是民俗学的一种分支或延伸,一称“后民俗学”。
在被各种歧义与悖论充分发挥之后,非遗学该站出来说明自己了。
非遗学的立场
如上所说,由于民俗学与新崛起的非遗学面对的是同一对象——民间文化,由于最初参与非遗抢救、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基本来自民俗学界,人们便顺理成章地认为,非遗只是民俗学遇到了一项时代性和社会性的工作,自然还在民俗学的范畴之内。
可是一些敏锐的学者发现,这项史无前例的工作,较之以往的民俗学大不相同。不仅所做的事情不同,其性质、方法、目的也完全不同。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向云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出版。这是最早对于非遗知识体系进行建构和描述的著作,今天看来,已具非遗学的基本形态。而这一年无论是国际还是中国非遗事业都才刚刚起步。这部书表明了我国学界的学术的敏感,视野的开阔和极强的开创性。它不仅展示了一个崭新而辽阔的学术空间,而且显现了一个学术立场——非遗学立场。这是一个有别于民间文化学和民俗学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遗产。可惜我们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部书深在的意义。
学术的立场是学术的出发点,也是学术的原点。它决定着学术的性质、内容、方法与目的。从不同立场出发,我们看到的事物的特征、要素、规律、功能、意义就会完全不同。就像对于一个人,周围不同的人从各自的立场(不同的身份、地位、利益、观念等)出发,看到的人物就会全然不同。
站在遗产这个立场来看,我们所做的非遗的认定、抢救和保护,绝不是对民间文化做一轮重新的调查和整理,而是要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财富“摸清家底”,这个家底就是遗产。这个工作过去从来没做过。
这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全新的立场,全新的视角,全新的有待探索与构建的学术。这个学术就是非遗学。
回过头来,还要再讨论一下遗产的概念与人类的遗产观。这有助于我们对非遗学的认识。
在人类传统的概念中,遗产是指先人留下的私人化的财富。主要是物质性财富。但是在20世纪后半期这个传统的遗产观渐渐发生了变化。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在《法国对遗产的认识过程》中写道:“在过去的二十年,遗产的概念已经扩大,发生了变化。旧的概念把遗产认定为父母留给子女的财物,新的概念被认为是社会整体的继承物。”
父母留给子女的是私人遗产或家庭遗产;社会整体继承的是公共遗产,即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必须由社会保护和传承下去。
正是出于这个遗产观,联合国制定了第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人类在文化遗产保护上迈出了第一步。然而,这第一步所保护的文化遗产只是物质性的,主要是历史建筑、考古遗址、文物。那时人们还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后来,人们渐渐发现了“非遗”。这使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变成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部分。
物质文化遗产是前一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珍贵的历史见证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传承至今并依然活着的文化生命。
这便构成了人类当代的遗产观。
非遗学,正是从遗产的立场出发,来认识民间文化的。但不是所有的民间文化都是非遗。非遗是其中历史文化的代表作,是当代遴选与认定的必须传承的文化经典。
是不是遗产是不同的。当一个事物有了遗产的属性,便多了一种性质、意义、价值,多了一种社会功能。这些都不是民俗学所能解释的。一件事物可以同时身在不同的知识范畴,从属于不同的学术范畴。比如佛罗伦萨花之圣母大教堂,既属于建筑学的经典,也属于遗产学的瑰宝。它们既有共同的文化内涵,也有各自的学术关切。建筑学关注它建筑的构造、设计、美学特征与创造性;遗产学更关注它自身的历史特征、档案、等级、保护重点与方法,以及如何传承得久远。非遗学更关注它的存在与生命,是保护和延续它生命的科学,一个此前没有的学科。
决定非遗学独立性的根本是——遗产。
学科的使命与特征
学术是具有使命的。对于非遗学,使命二字尤为重要。它不仅在学者身上,还在学术本身。这也是遗产的本质决定的。遗产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也是我们留给后人的,我们要好好享用它,还要把它完好地交给后人,中间不能损坏。特别是非遗,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很容易变异和丢失,要分外呵护好和传承好,这个使命理所当然就落在非遗学中了。民俗学没有这个使命。民俗学的使命是记录民众生活和建构民间文化,再往深处是探寻和呈现一个民族的民族性。
民俗学注重民俗事象的过去,非遗学注重非遗活生生的现在。民俗学把民间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在民俗学者眼中,民间文化是相对静止的、稳定的、很少变化的。非遗学者把非遗作为一种文化生命;在非遗学者眼中,非遗是活态的、动态的、应用的,在时代转型中充满不确定性。民俗学的工作是总结历史与描述现在,而非遗学则要通过对现存的非遗的研究,来探索它们通往明天的合理的道路。
就像医学是为了守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一样,非遗学是为了非遗生命的存续、文化命脉的延续。学科的使命决定了学科的特征。于是,非遗学的使命首先决定了它的工具性。非遗学具有很强的工具性。
它既是一种纯学术,追求精准、清晰、完整、谨严、高深;又是一种工具理论,为非遗构建知识,为非遗排难解纷,因而与当下的非遗的保护实践息息相通和紧密相关。非遗学毫不隐讳要直接为非遗服务,甚至为非遗所应用。
为此,非遗学是一门田野科学。在田野中认知,在田野中发现,在田野中探索,在田野中生效,从始至终都在田野。如果只是在田野采风和搜集材料,就不是非遗学了。
非遗学的教育也必须在田野中进行。田野就是民间,就是活生生的民间文化。只有问道于田野,才能得到切实的答案,才能感悟到非遗的精髓与神韵,彻悟到非遗的需要,以及非遗学的学术使命是什么。
不肩负学术使命的是伪非遗学。因此说,非遗教育中一定包含着责任教育。非遗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两种人才。一是非遗的研究人才,二是非遗的管理人才。然而,对于本世纪初刚刚进入人类保护视野的非遗,既缺乏研究乃至认知,更缺少科学的管理和管理的人才。非遗学的学术使命肩负着现实的紧迫性。
核心工作
面对非遗,非遗学有三项核心工作,是重中之重:其一,立档;其二,保护;其三,传承。立档主要是对非遗的历史而言,保护是永远首要的主题,传承是为了遗产的延续与永在。在非遗学中这三项工作既是工作实际,更是核心的学术内容。
立档 立档是指建立档案。民间文化是大众为自己创造的文化。自然流传,不传辄亡,自生自灭,没有记载,各种应用的器物也很少存惜。一种民俗或民艺一旦消泯,便了无痕迹。如果本世纪的前十年没有大规模非遗抢救和“保护名录”的建立,恐怕大量非遗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没有历史文献和档案是非遗的一个重大问题,故而非遗学首要的工作是为每一项非遗制作档案。
这里说的档案,不是政府部门的管理档案,是非遗学的学术资料性的存录。立档本身也是学术工作,是最根本最基础的工作。
档案存录历史,也为明天存录今天。
怎样的档案才是理想的档案?非遗学起步晚,没有太好的实例。民俗学中,著名的芬兰文学学会的口传文学资料档案库是一个极好的范例,但口头文学是一个例外,因为口头文学有搜集文本,又有书面文学做参考。其它非遗就复杂多了,构成不同,各有特点,立档时调查记录的方法必须与非遗各自不同的特点相结合,每种非遗档案便都是个案。同时,资料的整理和档案的编制必须专业化。由于我国非遗的形式太过纷繁,立档的规范是要首先研究和确定的。
现今我国已知非遗超过十万项,但保护力量十分有限。大多数非遗没有建立起系统的科学保护。如果不做存录,不做收集、调查、整理,没有立档,一旦传承受阻,瓦解失散,了无存证,才是真正的消亡。比如一些五十年前还“活着”的民间戏曲,如今消亡后没有档案,其面貌已无从得知。
非遗是活态存在,各种原因都可致其消亡,这就给海量的非遗的存录和立档增加了时间的压力。
保护 非遗保护是非遗学核心的核心。非遗学要为非遗的保护进行探索和研究,提供科学的理念、标准与方法。
自从2006年我国建立了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保护已成为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关键词。全民的现代文明的遗产观开始形成,文化自觉已经显现。遗产保护的终极目标是: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保护原真性是指物质遗产的保存完整和附着遗产上的历史文化信息不丢失。保护原生态是指保留住非遗的原本的文化形态与生命状态。原生态的判定是关键。但很多非遗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判,保护标准没有确定。如果保护没有凭据,是很容易得而复失的。保护标准的确定必须要有学术支撑。
关于保护方式,多年来已做过不少探索与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2011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简称《非遗法》),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法律保证。此外还有名录保护、制度保护、传承人保护、博物馆保护、教育保护等,渐成体系。这些保护都发挥了作用,同时都没有能够抵制住现代市场社会和旅游经济带来的强势冲击。这些都是非遗学直接面对的重要课题。非遗保护需要非遗学提供的主要是科学的理念,以及相关的标准、规则和专业的方法。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非遗学通过什么途径作用于保护实践?
传承 民俗学和遗产学对待传承这个概念的态度不同。民俗学认为传承是顺其自然的,是一个个民俗或民艺事象流传下来的民间方式。民俗学不人为地介入民间文化传承。非遗学则不然,为了非遗存在下去,一定要促其传承。
可是,这个“促”是人为的,如何“促”才不是负面干预的?如何做才是科学而非反科学的?这需要非遗学自己来回答来解决。
非遗的传承在当代碰到一个令人挠头的问题,也是一个时代的难题:非遗原本是来自民间的一种精神和文化的需要,或者说非遗是百姓的一种精神文化生活。但是到了市场经济时代,这种富于魅力的地方文化难免被转化为旅游工具和旅游商品。这种转化,会使非遗不知不觉地与原本的精神需求脱钩,最后留给游人的便只是一种观赏性的原形态,而没有精神性的原生态了。在当代,世界各地旅游地区的民俗与民艺所碰到的是同一个问题,这是非遗面临的无法绕开的困扰。如果非遗的内涵与功能发生了质变,会不会名存实亡?那么,非遗到底要传承什么?哪些必须恪守不变?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存在与传承?面对这类时代性的挑战,非遗学必须在思想和理论上做出切实和有效的应对。
这三项工作,都是非遗学核心的工作,核心的学术问题,也是其学科价值之所在。
【未完待续】
(作者系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
非遗学是一个新学科,一个独立的学科。本文作者冯骥才,是中国非遗保护事业的开创者,更是倡导者和实践者。区区万言,却是他几十年实践与思考的凝练,无疑将为非遗学者和从业者指出前行的方向和方法。本刊将以上下两篇的形式,分两期刊发全文,以飨读者。
非遗学是一个新学科,一个独立的学科。本文试图阐述它无可辩驳的独立性,它的学术本质,从元理论角度勾勒出非遗学卓尔不群的学科样貌。
一个新学科在刚刚确立时,常常会被怀疑它的独立性。新学科的倡导者们必然要遭遇挑战,不时会被诘问:非遗不就是民间文化吗?有必要另设一个学科吗?它本身能否成为一个学科?它具备足够的材料盖一座高楼大厦吗?
若要做出有力的回答还要靠新学科自己。
非遗的缘起
首先要说,非遗学的怀疑者毫无疑问是被历史误导了。
这个历史是在“非遗”诞生的过程中发生的。
20世纪后半期,人类开始认识到前人留下的历史创造中,除去物质性的遗址、建筑、器物、艺术品之外,还有大量精神性的遗产保存在代代相传的口头、活态、无形的行为与技艺中。它们和物质遗存一样,同样是必须永远保存的历史财富。然而人类任何一个伟大的自我认识,最初都是知音寥寥,非常孤寂。这些具有先觉意义的认知,最先只在日本与韩国等一些国家的学者中,直到本世纪初才渐渐得到国际的共识。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类文化遗产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是公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被简称为“非遗”。
历史地说,非遗是一个伟大的概念。它的诞生,表明人类对历史遗产认识的一个新高度,一个新突破,一个新发现;它发现了人类在已知的物质文化遗产之外,还有一宗极其巨大、绚丽多姿、活态的历史遗产,这便使它得到抢救和保护,免于在时代的更迭中泯灭。这是人类一次伟大的文化自觉,是文明史上一个伟大的进步。
早在非遗概念出现之前,人们将这一类型和范畴的文化称为“民间文化”,并建立起相应的科学而完整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譬如民俗学、民艺学、民间文化学等。
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民间文化的生长非常缓慢。它不是发展的模式,而是一种积淀的模式。它一直保持着相当稳定甚至是一种恒定的状态。然而,工业革命以来就不同了,社会骤然转型,固有的民间文化开始瓦解。这一变化在我国来得晚一些,到了20世纪后期,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冲击,民间文化才快速消散和面临濒危,致使一些敏感而先觉的人士与学者急切地呼吁抢救和保护。此时,对民间文化的称呼也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过的改变,比如在“民间文化”后边加上“遗产”二字,称为“民间文化遗产”;再比如本世纪初进行的大规模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于是,这一时期(21世纪初),同时出现两个概念:民间文化遗产和非遗。这两个概念本质相同,不同的是,民间文化遗产的概念来自学界,非遗的概念来自政府,因为非遗是由各国政府共同确定的。
政府作为遗产的第一责任人,为了便于对遗产进行管理,必须将遗产分类。于是文化遗产被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物质性的文化遗产,一种是非物质性的文化遗产,即非遗。可是,非遗是个新概念,需要知识支撑;由于非遗与民间文化在客观上是同一事物、同一范畴,故而,非遗最初使用的知识,都是从现成的民俗学、艺术学去拿。连国家制定非遗名录的分类,也参考了民俗学与艺术学的分类法;甄选和评定国家非遗的标准,也大多来自资深的民俗学者和艺术学者的修养与经验。这样,人们自然以为非遗只是一种政府称呼或官方概念。进而认为,所谓的非遗学不过是政府遗产保护不成体系的工具论而已;非遗学没有完整的知识,最多是民俗学的一种分支或延伸,一称“后民俗学”。
在被各种歧义与悖论充分发挥之后,非遗学该站出来说明自己了。
非遗学的立场
如上所说,由于民俗学与新崛起的非遗学面对的是同一对象——民间文化,由于最初参与非遗抢救、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基本来自民俗学界,人们便顺理成章地认为,非遗只是民俗学遇到了一项时代性和社会性的工作,自然还在民俗学的范畴之内。
可是一些敏锐的学者发现,这项史无前例的工作,较之以往的民俗学大不相同。不仅所做的事情不同,其性质、方法、目的也完全不同。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向云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出版。这是最早对于非遗知识体系进行建构和描述的著作,今天看来,已具非遗学的基本形态。而这一年无论是国际还是中国非遗事业都才刚刚起步。这部书表明了我国学界的学术的敏感,视野的开阔和极强的开创性。它不仅展示了一个崭新而辽阔的学术空间,而且显现了一个学术立场——非遗学立场。这是一个有别于民间文化学和民俗学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遗产。可惜我们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部书深在的意义。
学术的立场是学术的出发点,也是学术的原点。它决定着学术的性质、内容、方法与目的。从不同立场出发,我们看到的事物的特征、要素、规律、功能、意义就会完全不同。就像对于一个人,周围不同的人从各自的立场(不同的身份、地位、利益、观念等)出发,看到的人物就会全然不同。
站在遗产这个立场来看,我们所做的非遗的认定、抢救和保护,绝不是对民间文化做一轮重新的调查和整理,而是要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财富“摸清家底”,这个家底就是遗产。这个工作过去从来没做过。
这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全新的立场,全新的视角,全新的有待探索与构建的学术。这个学术就是非遗学。
回过头来,还要再讨论一下遗产的概念与人类的遗产观。这有助于我们对非遗学的认识。
在人类传统的概念中,遗产是指先人留下的私人化的财富。主要是物质性财富。但是在20世纪后半期这个传统的遗产观渐渐发生了变化。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在《法国对遗产的认识过程》中写道:“在过去的二十年,遗产的概念已经扩大,发生了变化。旧的概念把遗产认定为父母留给子女的财物,新的概念被认为是社会整体的继承物。”
父母留给子女的是私人遗产或家庭遗产;社会整体继承的是公共遗产,即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必须由社会保护和传承下去。
正是出于这个遗产观,联合国制定了第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人类在文化遗产保护上迈出了第一步。然而,这第一步所保护的文化遗产只是物质性的,主要是历史建筑、考古遗址、文物。那时人们还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后来,人们渐渐发现了“非遗”。这使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变成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部分。
物质文化遗产是前一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珍贵的历史见证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传承至今并依然活着的文化生命。
这便构成了人类当代的遗产观。
非遗学,正是从遗产的立场出发,来认识民间文化的。但不是所有的民间文化都是非遗。非遗是其中历史文化的代表作,是当代遴选与认定的必须传承的文化经典。
是不是遗产是不同的。当一个事物有了遗产的属性,便多了一种性质、意义、价值,多了一种社会功能。这些都不是民俗学所能解释的。一件事物可以同时身在不同的知识范畴,从属于不同的学术范畴。比如佛罗伦萨花之圣母大教堂,既属于建筑学的经典,也属于遗产学的瑰宝。它们既有共同的文化内涵,也有各自的学术关切。建筑学关注它建筑的构造、设计、美学特征与创造性;遗产学更关注它自身的历史特征、档案、等级、保护重点与方法,以及如何传承得久远。非遗学更关注它的存在与生命,是保护和延续它生命的科学,一个此前没有的学科。
决定非遗学独立性的根本是——遗产。
学科的使命与特征
学术是具有使命的。对于非遗学,使命二字尤为重要。它不仅在学者身上,还在学术本身。这也是遗产的本质决定的。遗产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也是我们留给后人的,我们要好好享用它,还要把它完好地交给后人,中间不能损坏。特别是非遗,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很容易变异和丢失,要分外呵护好和传承好,这个使命理所当然就落在非遗学中了。民俗学没有这个使命。民俗学的使命是记录民众生活和建构民间文化,再往深处是探寻和呈现一个民族的民族性。
民俗学注重民俗事象的过去,非遗学注重非遗活生生的现在。民俗学把民间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在民俗学者眼中,民间文化是相对静止的、稳定的、很少变化的。非遗学者把非遗作为一种文化生命;在非遗学者眼中,非遗是活态的、动态的、应用的,在时代转型中充满不确定性。民俗学的工作是总结历史与描述现在,而非遗学则要通过对现存的非遗的研究,来探索它们通往明天的合理的道路。
就像医学是为了守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一样,非遗学是为了非遗生命的存续、文化命脉的延续。学科的使命决定了学科的特征。于是,非遗学的使命首先决定了它的工具性。非遗学具有很强的工具性。
它既是一种纯学术,追求精准、清晰、完整、谨严、高深;又是一种工具理论,为非遗构建知识,为非遗排难解纷,因而与当下的非遗的保护实践息息相通和紧密相关。非遗学毫不隐讳要直接为非遗服务,甚至为非遗所应用。
为此,非遗学是一门田野科学。在田野中认知,在田野中发现,在田野中探索,在田野中生效,从始至终都在田野。如果只是在田野采风和搜集材料,就不是非遗学了。
非遗学的教育也必须在田野中进行。田野就是民间,就是活生生的民间文化。只有问道于田野,才能得到切实的答案,才能感悟到非遗的精髓与神韵,彻悟到非遗的需要,以及非遗学的学术使命是什么。
不肩负学术使命的是伪非遗学。因此说,非遗教育中一定包含着责任教育。非遗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两种人才。一是非遗的研究人才,二是非遗的管理人才。然而,对于本世纪初刚刚进入人类保护视野的非遗,既缺乏研究乃至认知,更缺少科学的管理和管理的人才。非遗学的学术使命肩负着现实的紧迫性。
核心工作
面对非遗,非遗学有三项核心工作,是重中之重:其一,立档;其二,保护;其三,传承。立档主要是对非遗的历史而言,保护是永远首要的主题,传承是为了遗产的延续与永在。在非遗学中这三项工作既是工作实际,更是核心的学术内容。
立档 立档是指建立档案。民间文化是大众为自己创造的文化。自然流传,不传辄亡,自生自灭,没有记载,各种应用的器物也很少存惜。一种民俗或民艺一旦消泯,便了无痕迹。如果本世纪的前十年没有大规模非遗抢救和“保护名录”的建立,恐怕大量非遗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没有历史文献和档案是非遗的一个重大问题,故而非遗学首要的工作是为每一项非遗制作档案。
这里说的档案,不是政府部门的管理档案,是非遗学的学术资料性的存录。立档本身也是学术工作,是最根本最基础的工作。
档案存录历史,也为明天存录今天。
怎样的档案才是理想的档案?非遗学起步晚,没有太好的实例。民俗学中,著名的芬兰文学学会的口传文学资料档案库是一个极好的范例,但口头文学是一个例外,因为口头文学有搜集文本,又有书面文学做参考。其它非遗就复杂多了,构成不同,各有特点,立档时调查记录的方法必须与非遗各自不同的特点相结合,每种非遗档案便都是个案。同时,资料的整理和档案的编制必须专业化。由于我国非遗的形式太过纷繁,立档的规范是要首先研究和确定的。
现今我国已知非遗超过十万项,但保护力量十分有限。大多数非遗没有建立起系统的科学保护。如果不做存录,不做收集、调查、整理,没有立档,一旦传承受阻,瓦解失散,了无存证,才是真正的消亡。比如一些五十年前还“活着”的民间戏曲,如今消亡后没有档案,其面貌已无从得知。
非遗是活态存在,各种原因都可致其消亡,这就给海量的非遗的存录和立档增加了时间的压力。
保护 非遗保护是非遗学核心的核心。非遗学要为非遗的保护进行探索和研究,提供科学的理念、标准与方法。
自从2006年我国建立了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保护已成为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关键词。全民的现代文明的遗产观开始形成,文化自觉已经显现。遗产保护的终极目标是: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保护原真性是指物质遗产的保存完整和附着遗产上的历史文化信息不丢失。保护原生态是指保留住非遗的原本的文化形态与生命状态。原生态的判定是关键。但很多非遗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判,保护标准没有确定。如果保护没有凭据,是很容易得而复失的。保护标准的确定必须要有学术支撑。
关于保护方式,多年来已做过不少探索与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2011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简称《非遗法》),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法律保证。此外还有名录保护、制度保护、传承人保护、博物馆保护、教育保护等,渐成体系。这些保护都发挥了作用,同时都没有能够抵制住现代市场社会和旅游经济带来的强势冲击。这些都是非遗学直接面对的重要课题。非遗保护需要非遗学提供的主要是科学的理念,以及相关的标准、规则和专业的方法。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非遗学通过什么途径作用于保护实践?
传承 民俗学和遗产学对待传承这个概念的态度不同。民俗学认为传承是顺其自然的,是一个个民俗或民艺事象流传下来的民间方式。民俗学不人为地介入民间文化传承。非遗学则不然,为了非遗存在下去,一定要促其传承。
可是,这个“促”是人为的,如何“促”才不是负面干预的?如何做才是科学而非反科学的?这需要非遗学自己来回答来解决。
非遗的传承在当代碰到一个令人挠头的问题,也是一个时代的难题:非遗原本是来自民间的一种精神和文化的需要,或者说非遗是百姓的一种精神文化生活。但是到了市场经济时代,这种富于魅力的地方文化难免被转化为旅游工具和旅游商品。这种转化,会使非遗不知不觉地与原本的精神需求脱钩,最后留给游人的便只是一种观赏性的原形态,而没有精神性的原生态了。在当代,世界各地旅游地区的民俗与民艺所碰到的是同一个问题,这是非遗面临的无法绕开的困扰。如果非遗的内涵与功能发生了质变,会不会名存实亡?那么,非遗到底要传承什么?哪些必须恪守不变?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存在与传承?面对这类时代性的挑战,非遗学必须在思想和理论上做出切实和有效的应对。
这三项工作,都是非遗学核心的工作,核心的学术问题,也是其学科价值之所在。
【未完待续】
(作者系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
版权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作为参考,不代表本站观点。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果网站中图片和文字侵犯了您的版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处理!转载本站内容,请注明转载网址、作者和出处,避免无谓的侵权纠纷。
上一篇:冯骥才:非遗学原理(下)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