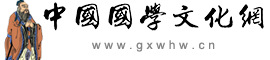栏目: 国学理论 作者:佚名 热度:
古今中外,卓越思想的产生离不开三个因素:时、地、人。因此,阐释、评价、应用一种思想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如上三个因素。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所得结论都将有失科学、客观、公允。但是在先秦诸子研究中,更多的目光投注到“时”——春秋战国和“人”——诸子群体,而对“地”——由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构成的地域文化却关注不多。《汉书·艺文志》从“时”“人”出发,以“诸子出于王官”解释先秦诸子的产生,后世认可、追随者甚众。《淮南子·要略》基于“时”“地”回答同一问题,卓成一家,且早于“王官说”,影响却远不如前者。原因固然多种,但对地域文化之于先秦诸子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应是其一。
先秦诸子研究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诸子何以产生、因何不同、如何评价。忽视地域文化,任何一个都很难获得满意答案。
地域文化是回答先秦诸子何以产生、因何不同的重要视角,这一点在先秦法家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显著。《淮南子·要略》解释儒、墨、管子、晏子、纵横、申子、商鞅等七个(家)诸子的产生,涉及地域文化者有三:管子、申子、商子。《要略》认为齐国负海障河,地狭田少,民多智巧是《管子》产生的重要原因;韩国介于大国之间,地墽民险,生存不易,重视法治,从而促使申子刑名之学产生;秦国被险带河,地利形便,寡义趋利,因而商鞅之法得以施行。申、商之学属先秦法家无疑。与管仲相关的《管子》归属虽有争议,但内容上的以法治国特色,频见于古籍的“管韩”“商管”合称,以及包括刘歆《七略》在内的历代书目多将其列入子部法家类的事实,可证《管子》的法家属性。如此一来即可发现,《淮南子》唯在解释法家发生时用到了地域文化。结合地域文化和法家研究史看,这并非偶然。相反,它在说明着一个事实:相对其他先秦诸子,法家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
中国的地域文化意识产生很早,但形成自觉则到了魏晋,研究高峰出现在明清之际。具体到先秦诸子就更晚一些。清季民初,西学东渐,受西方各种“地理学+”理论影响,以地域文化为视角阐释先秦诸子成为热点。王国维率先提出诸子分南北,梁启超、刘师培、蒙文通等继之对先秦诸子与地域文化关系展开细致全面的探讨,法家依然是重点。
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指出,诸子不仅有南北分野,还有东西不同,“商、韩之在西,管、驺之在东,或主峻刻,或崇虚无”(《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930页)。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他专门从地域文化切入,就管商韩学说发表见解,认为齐与秦晋地域文化促使国家观念产生,国家需要法律,因而衍生出法家思想。但是,齐和秦晋的自然地理文化并不相同。齐国临海,秦晋环山,濒海之民和陆居之民在性情、习俗、生产方式等方面均异,故二地的法家思想有别。这就从地域文化角度阐明了法家何以在齐和秦晋产生、为何《管子》和申商韩的法家思想不同,可谓与《淮南子·要略》遥相呼应。为了对两种法家加以区分,梁启超称《管子》为齐派(北东派),申商韩为秦晋派(北西派),这是后来冯友兰“齐法家”“晋法家”称谓的雏形。
刘师培于1905年撰写《南北学派不同论》总论古代学术与地域文化的关系,首论先秦诸子,诸子中又首论法家。和梁启超相同,刘师培注意到了同为法家的《管子》与申商韩之说的不同,并认为这种不同乃地域文化所致。
在民国先秦诸子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中,蒙文通也是一位重要学者。其观点与梁启超、刘师培同中有异。相同的是他也认为地域文化在先秦诸子的产生和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域殊则性俗异,性俗异则为说不同,先秦学术其大略固是耳。”(《古史甄微》,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635页)具体到法家则是“法家之士多出于三晋,而其功显于秦”,其本于“西北民族之教”(627页)。不同的是蒙文通视位于东方的齐、鲁为中国文化发祥地、泉源、重心,由此又得出“法家者流,此东方之北方文化;道家者流,此东方之南方文化;儒家者流,此东方之东方文化”(400页),于是产生于齐地的《管子》被列入儒家,这显然不合《管子》内容,也消解了《管子》与齐地独特地域文化的关系。
研究先秦诸子,不能不涉及对诸子的评价和定位。就法家而言,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因为自汉至今,对法家的评价始终呈现出冰火两重的极端化特点。有将法家妖魔化、污名化而挞伐者,有视其为治国良方而大加称赞者。这两种观点均有违学术理性,与法家真实不符。究其原因,在于对法家缺乏深度理解,表现之一仍是对地域文化在法家研究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中国自古疆域辽阔,可分为若干文化区,齐、晋地域文化在形成初期就表现出独特之处。武王克商立周后,为稳固新政权“封建亲戚,以蕃屏周”。齐国的任务是绥靖周朝东部,晋国则要保证北方的稳定,齐、晋因此成为两个特殊的诸侯国:远离王室,担负重任,周边或被夷人和殷商旧属或被夏民和戎狄包围,处境异常艰难。当中原各国在思考发展问题时,齐、晋却要直面自身的生死存亡和王朝安危。齐为此“因其俗,简其礼”,晋则“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种因地制宜、求同存异的治国策略体现出周朝君臣高超的政治智慧。齐、晋迅速崛起壮大。这一过程中,在齐,东夷、殷商、姜戎诸种文化与周文化融合;在晋,夏、戎狄、殷商等文化与周文化汇聚,最终形成了以尚利重功、崇尚法度、富于变革为特点的齐、晋地域文化,这正是适合法家生根发芽的沃土。早期孕育形成的文化特点决定了此后齐、晋文化的走向,以管商韩为代表的法家在此产生可谓水到渠成。因此,可以说离开地域文化无以谈法家。
先秦法家的产生和存在只是一种现象,现象背后的时、地、人等因素才是问题的根本。“地”在其中最为关键。因为法家的要义是以法治国,而法律的制定不仅要适合政体旨趣,同时还需考虑地理位置、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诸多地域文化因素。所以,讲好、用好法家“故事”不能不关注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深入、客观、理性认识和评判法家不可或缺的前提。
(作者:杨玲,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先秦诸子研究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诸子何以产生、因何不同、如何评价。忽视地域文化,任何一个都很难获得满意答案。
地域文化是回答先秦诸子何以产生、因何不同的重要视角,这一点在先秦法家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显著。《淮南子·要略》解释儒、墨、管子、晏子、纵横、申子、商鞅等七个(家)诸子的产生,涉及地域文化者有三:管子、申子、商子。《要略》认为齐国负海障河,地狭田少,民多智巧是《管子》产生的重要原因;韩国介于大国之间,地墽民险,生存不易,重视法治,从而促使申子刑名之学产生;秦国被险带河,地利形便,寡义趋利,因而商鞅之法得以施行。申、商之学属先秦法家无疑。与管仲相关的《管子》归属虽有争议,但内容上的以法治国特色,频见于古籍的“管韩”“商管”合称,以及包括刘歆《七略》在内的历代书目多将其列入子部法家类的事实,可证《管子》的法家属性。如此一来即可发现,《淮南子》唯在解释法家发生时用到了地域文化。结合地域文化和法家研究史看,这并非偶然。相反,它在说明着一个事实:相对其他先秦诸子,法家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
中国的地域文化意识产生很早,但形成自觉则到了魏晋,研究高峰出现在明清之际。具体到先秦诸子就更晚一些。清季民初,西学东渐,受西方各种“地理学+”理论影响,以地域文化为视角阐释先秦诸子成为热点。王国维率先提出诸子分南北,梁启超、刘师培、蒙文通等继之对先秦诸子与地域文化关系展开细致全面的探讨,法家依然是重点。
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指出,诸子不仅有南北分野,还有东西不同,“商、韩之在西,管、驺之在东,或主峻刻,或崇虚无”(《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930页)。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他专门从地域文化切入,就管商韩学说发表见解,认为齐与秦晋地域文化促使国家观念产生,国家需要法律,因而衍生出法家思想。但是,齐和秦晋的自然地理文化并不相同。齐国临海,秦晋环山,濒海之民和陆居之民在性情、习俗、生产方式等方面均异,故二地的法家思想有别。这就从地域文化角度阐明了法家何以在齐和秦晋产生、为何《管子》和申商韩的法家思想不同,可谓与《淮南子·要略》遥相呼应。为了对两种法家加以区分,梁启超称《管子》为齐派(北东派),申商韩为秦晋派(北西派),这是后来冯友兰“齐法家”“晋法家”称谓的雏形。
刘师培于1905年撰写《南北学派不同论》总论古代学术与地域文化的关系,首论先秦诸子,诸子中又首论法家。和梁启超相同,刘师培注意到了同为法家的《管子》与申商韩之说的不同,并认为这种不同乃地域文化所致。
在民国先秦诸子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中,蒙文通也是一位重要学者。其观点与梁启超、刘师培同中有异。相同的是他也认为地域文化在先秦诸子的产生和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域殊则性俗异,性俗异则为说不同,先秦学术其大略固是耳。”(《古史甄微》,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635页)具体到法家则是“法家之士多出于三晋,而其功显于秦”,其本于“西北民族之教”(627页)。不同的是蒙文通视位于东方的齐、鲁为中国文化发祥地、泉源、重心,由此又得出“法家者流,此东方之北方文化;道家者流,此东方之南方文化;儒家者流,此东方之东方文化”(400页),于是产生于齐地的《管子》被列入儒家,这显然不合《管子》内容,也消解了《管子》与齐地独特地域文化的关系。
研究先秦诸子,不能不涉及对诸子的评价和定位。就法家而言,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因为自汉至今,对法家的评价始终呈现出冰火两重的极端化特点。有将法家妖魔化、污名化而挞伐者,有视其为治国良方而大加称赞者。这两种观点均有违学术理性,与法家真实不符。究其原因,在于对法家缺乏深度理解,表现之一仍是对地域文化在法家研究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中国自古疆域辽阔,可分为若干文化区,齐、晋地域文化在形成初期就表现出独特之处。武王克商立周后,为稳固新政权“封建亲戚,以蕃屏周”。齐国的任务是绥靖周朝东部,晋国则要保证北方的稳定,齐、晋因此成为两个特殊的诸侯国:远离王室,担负重任,周边或被夷人和殷商旧属或被夏民和戎狄包围,处境异常艰难。当中原各国在思考发展问题时,齐、晋却要直面自身的生死存亡和王朝安危。齐为此“因其俗,简其礼”,晋则“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种因地制宜、求同存异的治国策略体现出周朝君臣高超的政治智慧。齐、晋迅速崛起壮大。这一过程中,在齐,东夷、殷商、姜戎诸种文化与周文化融合;在晋,夏、戎狄、殷商等文化与周文化汇聚,最终形成了以尚利重功、崇尚法度、富于变革为特点的齐、晋地域文化,这正是适合法家生根发芽的沃土。早期孕育形成的文化特点决定了此后齐、晋文化的走向,以管商韩为代表的法家在此产生可谓水到渠成。因此,可以说离开地域文化无以谈法家。
先秦法家的产生和存在只是一种现象,现象背后的时、地、人等因素才是问题的根本。“地”在其中最为关键。因为法家的要义是以法治国,而法律的制定不仅要适合政体旨趣,同时还需考虑地理位置、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诸多地域文化因素。所以,讲好、用好法家“故事”不能不关注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深入、客观、理性认识和评判法家不可或缺的前提。
(作者:杨玲,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版权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作为参考,不代表本站观点。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果网站中图片和文字侵犯了您的版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处理!转载本站内容,请注明转载网址、作者和出处,避免无谓的侵权纠纷。
下一篇:三晋文化与法家起源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