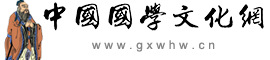栏目: 国学理论 作者:佚名 热度:
乡贤,指那些长期居住在乡村、不应察举与征辟或者在出仕以前或辞官以后不担任朝廷官职且以道德文章为乡人所推崇敬重者。汉末魏晋南北朝,王朝更迭频繁,国家政权的权力往往无法抵达社会的末端——乡村,造成乡村治理的缺失。在此种情况下,乡贤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乡村道德伦理的恢复和建设方面,体现得尤为显著。
汉末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失序与自治
自党锢事起,汉代社会原有的秩序被打破,特别是朝廷以政权权威建立的一整套法律制度的松弛,造成社会的失序。《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云:“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中常侍吕强言于帝曰:‘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帝惧其言,乃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其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随着曹操迎汉献帝都许,群雄逐鹿,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在失序的社会环境中,依托政权强力建立的由上而下、以各级行政机构为标识的社会治理体系崩坏瘫痪,丧失了承担社会治理的功能,作为传统社会最为重要的社会基层——乡村,基本依靠自治实现粗略的治理。北方地区的坞壁就是这种治理方式的代表。如《晋书》卷八八《孝友传·庾衮传》所载,庾衮曾两次主导建立乡村自治。第一次是齐王冏之乱时,张泓等肆掠于阳翟,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第二次是庾衮见晋室将乱,乃携其妻子适林虑山。
庾衮第一次率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典型的坞壁式自治,推主脑、建武装:“是时百姓安宁,未知战守之事,衮曰:‘孔子云: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乃集诸群士而谋曰:‘二三君子相与处于险,将以安保亲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不散则乱矣。将若之何?’众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谁!’衮默然有间,乃言曰:‘古人急病让夷,不敢逃难,然人之立主,贵从其命也。’”《晋书·庾衮传》所载比较典型地再现了坞壁的建立过程。只不过,庾衮所建,是临时性的,在张泓劫掠的威胁消失之后,这种自治也就解散了。
庾衮第二次携其妻子适林虑山的自治,是另一种形式,以表率的形式教化乡里,通过道德人伦的重建,实现一地秩序特别是人伦秩序的恢复。《晋书·庾衮传》云:“乃携其妻子适林虑山,事其新乡如其故乡,言忠信,行笃敬。比及期年,而林虑之人归之,咸曰庾贤。”这种自治是在社会相对安定的条件下自然形成,是乡贤的道德楷模和教化的结果。而当这种自治面临劫掠威胁时,向坞壁形式自治的转化是迅速的,乡贤也因其威望,自然成为其中的核心。庾衮在林虑时,后遭遇石勒攻掠,松散的乡村自治便迅速实现转化:“及石勒攻林虑,父老谋曰:‘此有大头山,九州之绝险也。上有古人遗迹,可共保之。’惠帝迁于长安,衮乃相与登于大头山而田于其下。年谷未熟,食木实,饵石蘂,同保安之,有终焉之志。”庾衮与乡人所归大头山,险绝偏僻,地势当易守难攻。且还可以耕种,这与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记的桃花源类似,以致庾衮产生“终焉之志”。
乡贤与乡村道德伦理秩序建设
作为道德文章楷模的乡贤在乡村自治中,特别是道德伦理秩序建设中,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
郭泰,字林宗,汉末名士,有人伦之鉴,题品海内之士,故为时人所敬重。郭泰乡人贾淑,“虽世有冠冕,而性险害,邑里患之”。郭泰丁母忧,贾淑来吊,而此时正好巨鹿高士孙威直也来吊念,不进而去。郭泰追而谢,向孙威直解释了为何允许贾淑吊念的原因:“贾子厚诚凶德,然洗心同善,仲尼不逆互乡,故许其进也。”而“淑闻之,改过自厉,终成善士”。(佚名《郭泰别传》,见熊明辑校《汉魏六朝杂传集》。下引同)郭泰并没有直接训导贾淑,而是在与孙威直的谈话中,透露对贾淑的期待,这种期待中蕴含郭泰对贾淑的内在良好品格的肯定,从而让贾淑实现自励改过。作为道德文章楷模的乡贤,表现出巨大的激励作用。
乡贤在汉末魏晋南北朝乡村失序的情况下,常常表现出巨大的凝聚力和道德感染力,从而以其德望,实现民风的转变。如三国时的王烈,字彦方。有盗牛者被抓获时,发誓改过自新,就要求“幸无使王烈闻之”。而受人帮助,探问姓名,也是要“请子告吾姓名,吾将以告王烈”。行为的非与是,不愿王烈知道或让王烈知道,其背后心理,体现了王烈在乡村道德评价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乡贤在乡村道德伦理建设中作用的发挥,方式是多样化的。最突出和系统化的方式是建学校。王烈就是首先通过建学校来推进乡村民风的转变:“遂建学校,敦崇庠序。其诱人也,皆不因其性气,诲之以道,使之从善远恶。益者不自觉,而大化隆行,皆成宝器。”再以这些学生为榜样影响乡里:“门人出入,容止可观,时在市井,行步有异,人皆别之。州闾成风,咸竞为善。”
其次是以言传身教式的榜样示范,促进民风的转变。如皇甫谧《高士传》所载管宁所居屯落,原来汲水,或男女杂错,或争井斗阋。管宁的做法是:“乃多买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来者得而怪之,问知宁所为,乃各相责,不复斗讼。”在管宁以身作则的礼让教化下,其所居之乡,“左右无斗讼之声,礼让移于海表”。实现了乡村民风的转变。
乡贤的权威及其赋予
乡贤在乡民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他们的评判具有权威性,《陈寔别传》云陈寔“在乡闾,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乡村中发生争讼,都要寻求陈寔的判正,而经过陈寔判正的,都心服口服,以至乡里流传这样的民谣:“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断。”
乡贤的权威无疑首先来自对人事的公平判断,即如《陈寔别传》所说陈寔的“平心率物”“晓譬曲直”。其次则是乡贤的道德文章,足以让人信赖。如《晋书·庾衮传》云庾衮“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训蒙幼,临人之丧必尽哀,会人之葬必躬筑,劳则先之,逸则后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乡党莫不崇仰,门人感慕”。王烈之所以为乡里所敬,与其“英名著于海内,道成德立”相关,与其在乡里的所行所履有关,一是孝:“还归旧庐,遂遭父丧,泣泪三年。”一是仁:“遇岁饥馑,路有饿殍,烈乃分釜庾之储,以救邑里之命。”正是这样的品格为乡里所认同,“是以宗族称孝,乡党归仁”,获得乡里的普遍信赖。王烈由此成为乡里的公平公正的象征,以至“时人或讼曲直,将质于烈,或至涂而反,或望庐而还,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闻之”,乡里也因此实现治理。
正是乡贤的道德文章,带动乡里良好民风的形成。三国时期邴原的例子颇为典型。邴原自幼“金玉其行”,因而为乡里所敬,后丧乱方炽,遂到辽东。《邴原别传》载,辽东多虎,原之邑落独无虎患;又得遗钱,拾以系树枝,而路树成社。于是便有里中耆老将此二事编成谚谣:“邴君行仁,落邑无虎;邴君行廉,路树成社。”邴原这种金玉般的品行,感染乡里,带动所居乡村良好民风的形成,而邴原本身,也成为当地良好民风的象征。
人们对乡贤的敬重,除了其个人的品行外,也在于其对当地的良好影响和由此带给当地的普遍道德提升。许多乡贤对当地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当这些乡贤移居时,整个部落都愿意跟随移居。比如邴原在辽东多年,欲还故乡,为公孙度所禁绝,邴原打算移居到靠近郡城之地,其所居屯落全部跟随他移居。蔡邕死后,据《蔡邕别传》,“东国宗敬邕,不言名,咸称蔡君。兖州、陈留并图画蔡邕形像而颂之曰:‘文同三闾,孝齐参骞。’”
(作者:熊明,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汉末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失序与自治
自党锢事起,汉代社会原有的秩序被打破,特别是朝廷以政权权威建立的一整套法律制度的松弛,造成社会的失序。《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云:“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中常侍吕强言于帝曰:‘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帝惧其言,乃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其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随着曹操迎汉献帝都许,群雄逐鹿,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在失序的社会环境中,依托政权强力建立的由上而下、以各级行政机构为标识的社会治理体系崩坏瘫痪,丧失了承担社会治理的功能,作为传统社会最为重要的社会基层——乡村,基本依靠自治实现粗略的治理。北方地区的坞壁就是这种治理方式的代表。如《晋书》卷八八《孝友传·庾衮传》所载,庾衮曾两次主导建立乡村自治。第一次是齐王冏之乱时,张泓等肆掠于阳翟,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第二次是庾衮见晋室将乱,乃携其妻子适林虑山。
庾衮第一次率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典型的坞壁式自治,推主脑、建武装:“是时百姓安宁,未知战守之事,衮曰:‘孔子云: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乃集诸群士而谋曰:‘二三君子相与处于险,将以安保亲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不散则乱矣。将若之何?’众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谁!’衮默然有间,乃言曰:‘古人急病让夷,不敢逃难,然人之立主,贵从其命也。’”《晋书·庾衮传》所载比较典型地再现了坞壁的建立过程。只不过,庾衮所建,是临时性的,在张泓劫掠的威胁消失之后,这种自治也就解散了。
庾衮第二次携其妻子适林虑山的自治,是另一种形式,以表率的形式教化乡里,通过道德人伦的重建,实现一地秩序特别是人伦秩序的恢复。《晋书·庾衮传》云:“乃携其妻子适林虑山,事其新乡如其故乡,言忠信,行笃敬。比及期年,而林虑之人归之,咸曰庾贤。”这种自治是在社会相对安定的条件下自然形成,是乡贤的道德楷模和教化的结果。而当这种自治面临劫掠威胁时,向坞壁形式自治的转化是迅速的,乡贤也因其威望,自然成为其中的核心。庾衮在林虑时,后遭遇石勒攻掠,松散的乡村自治便迅速实现转化:“及石勒攻林虑,父老谋曰:‘此有大头山,九州之绝险也。上有古人遗迹,可共保之。’惠帝迁于长安,衮乃相与登于大头山而田于其下。年谷未熟,食木实,饵石蘂,同保安之,有终焉之志。”庾衮与乡人所归大头山,险绝偏僻,地势当易守难攻。且还可以耕种,这与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记的桃花源类似,以致庾衮产生“终焉之志”。
乡贤与乡村道德伦理秩序建设
作为道德文章楷模的乡贤在乡村自治中,特别是道德伦理秩序建设中,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
郭泰,字林宗,汉末名士,有人伦之鉴,题品海内之士,故为时人所敬重。郭泰乡人贾淑,“虽世有冠冕,而性险害,邑里患之”。郭泰丁母忧,贾淑来吊,而此时正好巨鹿高士孙威直也来吊念,不进而去。郭泰追而谢,向孙威直解释了为何允许贾淑吊念的原因:“贾子厚诚凶德,然洗心同善,仲尼不逆互乡,故许其进也。”而“淑闻之,改过自厉,终成善士”。(佚名《郭泰别传》,见熊明辑校《汉魏六朝杂传集》。下引同)郭泰并没有直接训导贾淑,而是在与孙威直的谈话中,透露对贾淑的期待,这种期待中蕴含郭泰对贾淑的内在良好品格的肯定,从而让贾淑实现自励改过。作为道德文章楷模的乡贤,表现出巨大的激励作用。
乡贤在汉末魏晋南北朝乡村失序的情况下,常常表现出巨大的凝聚力和道德感染力,从而以其德望,实现民风的转变。如三国时的王烈,字彦方。有盗牛者被抓获时,发誓改过自新,就要求“幸无使王烈闻之”。而受人帮助,探问姓名,也是要“请子告吾姓名,吾将以告王烈”。行为的非与是,不愿王烈知道或让王烈知道,其背后心理,体现了王烈在乡村道德评价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乡贤在乡村道德伦理建设中作用的发挥,方式是多样化的。最突出和系统化的方式是建学校。王烈就是首先通过建学校来推进乡村民风的转变:“遂建学校,敦崇庠序。其诱人也,皆不因其性气,诲之以道,使之从善远恶。益者不自觉,而大化隆行,皆成宝器。”再以这些学生为榜样影响乡里:“门人出入,容止可观,时在市井,行步有异,人皆别之。州闾成风,咸竞为善。”
其次是以言传身教式的榜样示范,促进民风的转变。如皇甫谧《高士传》所载管宁所居屯落,原来汲水,或男女杂错,或争井斗阋。管宁的做法是:“乃多买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来者得而怪之,问知宁所为,乃各相责,不复斗讼。”在管宁以身作则的礼让教化下,其所居之乡,“左右无斗讼之声,礼让移于海表”。实现了乡村民风的转变。
乡贤的权威及其赋予
乡贤在乡民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他们的评判具有权威性,《陈寔别传》云陈寔“在乡闾,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乡村中发生争讼,都要寻求陈寔的判正,而经过陈寔判正的,都心服口服,以至乡里流传这样的民谣:“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断。”
乡贤的权威无疑首先来自对人事的公平判断,即如《陈寔别传》所说陈寔的“平心率物”“晓譬曲直”。其次则是乡贤的道德文章,足以让人信赖。如《晋书·庾衮传》云庾衮“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训蒙幼,临人之丧必尽哀,会人之葬必躬筑,劳则先之,逸则后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乡党莫不崇仰,门人感慕”。王烈之所以为乡里所敬,与其“英名著于海内,道成德立”相关,与其在乡里的所行所履有关,一是孝:“还归旧庐,遂遭父丧,泣泪三年。”一是仁:“遇岁饥馑,路有饿殍,烈乃分釜庾之储,以救邑里之命。”正是这样的品格为乡里所认同,“是以宗族称孝,乡党归仁”,获得乡里的普遍信赖。王烈由此成为乡里的公平公正的象征,以至“时人或讼曲直,将质于烈,或至涂而反,或望庐而还,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闻之”,乡里也因此实现治理。
正是乡贤的道德文章,带动乡里良好民风的形成。三国时期邴原的例子颇为典型。邴原自幼“金玉其行”,因而为乡里所敬,后丧乱方炽,遂到辽东。《邴原别传》载,辽东多虎,原之邑落独无虎患;又得遗钱,拾以系树枝,而路树成社。于是便有里中耆老将此二事编成谚谣:“邴君行仁,落邑无虎;邴君行廉,路树成社。”邴原这种金玉般的品行,感染乡里,带动所居乡村良好民风的形成,而邴原本身,也成为当地良好民风的象征。
人们对乡贤的敬重,除了其个人的品行外,也在于其对当地的良好影响和由此带给当地的普遍道德提升。许多乡贤对当地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当这些乡贤移居时,整个部落都愿意跟随移居。比如邴原在辽东多年,欲还故乡,为公孙度所禁绝,邴原打算移居到靠近郡城之地,其所居屯落全部跟随他移居。蔡邕死后,据《蔡邕别传》,“东国宗敬邕,不言名,咸称蔡君。兖州、陈留并图画蔡邕形像而颂之曰:‘文同三闾,孝齐参骞。’”
(作者:熊明,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版权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作为参考,不代表本站观点。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果网站中图片和文字侵犯了您的版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处理!转载本站内容,请注明转载网址、作者和出处,避免无谓的侵权纠纷。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