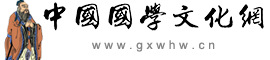栏目: 国学研究 作者:佚名 热度:
【考古中国】
考古学始终以研究古代遗址的结构与布局为首责,小到水井、房址,大到墓地、作坊,林林总总,都是构成遗址的核心要素。每一位考古学家都曾梦想把所有要素揭示清楚,但往往事与愿违,难以实现。如果加入时间与空间维度,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就更为复杂而持久,很多大型都城遗址都是几代考古人接续努力,才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甲骨文的故乡,商代晚期都城殷墟更是如此。
■百年殷墟考古,试图还原立体的殷墟都城生命史;
■“卫星城”的发现,突破了传统认知的殷墟范围,这兴许就是甲骨文、金文中的“大邑商”;
■发现道路、池苑、围沟,殷墟都邑内部结构探索有了新思路。
“兼及四邻”探索殷墟布局
殷墟甲骨文中,常有“大邑商”“天邑商”“中商”等记载,最早记录“中国”二字的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也明确提到“大邑商”。关于其确切的含义,自甲骨文发现以来,学者们就争议不休,莫衷一是。归纳学者的观点,我们能知晓“大邑商”“天邑商”可以泛指商王朝,也可以确指殷墟都城或王畿地区。但文献看到的多是一个“点”或“面”,无法从多学科、多维度、多视角、全方位深入研究立体的殷墟都城生命史。
自1928年开始发掘以来,厘清殷墟的结构、布局、年代与性质是历代殷墟考古人的主要工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除了宫殿与王陵发掘之外,李济、梁思永等就曾提出“兼及四邻”的思想,积极进行宫殿、王陵之外的探索;1950年后,配合城乡建设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在整个殷墟范围内全面展开,居址、作坊、墓地等不断发现,促使学者们开始思考都邑内部社会结构问题。学者们以殷墟不同阶段的考古新发现、新认识为基础,取得若干研究成果,比如:1979年,杨宝成、杨锡璋通过对殷墟西区近千座墓葬的研究,特别是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指出,殷人“聚族而居、合族而葬”;1995年郑若葵首次探讨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提出“大凡有殷代墓群出现的地方,都可能同时是某一族邑的所在地”。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历时二百余年的殷墟同样如此,它至少经历了初建、兴盛、衰落、废弃等过程。如果把时间维度考虑在内,那么殷墟都邑布局动态变化又会如何呢?2008年岳洪彬等分析更多的殷墟都邑布局元素,在肯定郑若葵提出的族邑模式的基础上指出,殷墟从早期的“点”不断扩展,最终连成“面”,族邑内部(包括宫殿区)具有很多共同的文化要素,如大型取土坑、夯土建筑、墓葬群、作坊、道路、灰坑、窖穴、水井等。2009年唐际根等进一步从聚落考古的角度指出,“洹河流域的商邑至少从规模上呈现明显的一大带众小结构”,在对典型商邑的遗迹构成分类梳理的基础上认为,“大邑商”系由密集分布的诸多小型商邑构成的王都,宫殿与王陵是“大邑商”的核心,道路与水渠是不同族邑的重要连接方式。2022年严志斌指出殷墟“族墓地”存在问题,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严志斌结合殷墟手工业作坊居住、生产与埋葬共存的现象认为,“工、居、葬合一”的工业作坊区模式,是殷墟都城内的主要聚落形态及基层社会组织,工业作坊区在商王族(包括多子族)控制下,以超血缘关系的人群从事手工业生产活动。
从一座都城到三级聚落群
近些年,在传统认知的洹北商城、殷墟区域之外又不断有新的重要考古发现,特别是诸如与洹北商城同时期的陶家营环壕聚落、与殷墟大体同时期的辛店超大型铸铜作坊遗址的发现,又促使大家追问何谓“大邑商”?解答这个世纪难题,还需以考古学为本位。
超大型都邑往往会受到更多的关注,但孤木难成林,都邑之所以能够运转,与相应区域内灿若星辰的中小型聚落是分不开的。采用聚落考古的理念与方法,来解决诸如何谓“大邑商”的问题,仍是有效而重要的手段与途径。宏观角度来讲,作为都邑的殷墟与王畿内外众多族邑、方国的关系问题,既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家治理模式的问题,也是超大型聚落与次级聚落的问题。如果把范围缩小到一个流域,遗址间的相互关系就会更加清晰、直观。洹北商城与殷墟所在的洹河流域曾进行过数次考古调查,其中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美联合调查队进行的调查成果丰硕,洹北商城是此次调查最大的收获。据此,唐际根等提出洹河流域“一大带众小”的布局模式。
2021年发现的陶家营遗址,位于洹北商城以北约4公里,面积近20万平方米。遗址东部围以方形环壕,面积近10万平方米。从勘探与发掘来看,陶家营遗址规模中等,遗址内功能分区较为明确,居址、作坊、墓地等分布井然有序。墓葬之内随葬的大量青铜礼器也表明该遗址的等级不低。这项重要发现,让我们重新审视洹北商城以西约1.4公里的殷墟王陵始建年代,以及洹河南岸20世纪30年代发掘的“小屯五座墓”及“甲组基址”的年代与性质问题。二者也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老大难”问题。
陶家营遗址的发现也让我们转换了思路:与洹北商城470余万平方米庞大的体量相比,商代中期的陶家营与小屯遗址应是洹北商城周边的二级聚落,王陵区78M1墓葬年代表明,王陵始建年代对应洹北商城阶段;安阳县西蒋村遗址等零星的发掘也表明,规模更小的商代中期遗址同样存在;这样就大体形成了洹河流域商代中期三级聚落的社会结构。当然,以后随着考古调查与发掘材料的不断丰富,聚落层次可能会更丰富、更立体。
2016年,在距殷墟宫殿区直线距离10公里处,新发现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辛店遗址,勘探与发掘表明,这里是殷墟目前所知最大的青铜作坊遗址,面积达50万平方米。青铜器铭文表明,从事青铜铸造的家族主要是“戈”族。作坊内部呈现生产、生活与墓葬混杂在一起的布局方式。除辛店遗址外,甚至在传统认知的殷墟分布区的西南、东南等很远的地方,同样发现规模较大、等级不低的晚商时期遗址。这些新发现虽都属洹河流域,但基本远离了历次洹河流域调查时所强调的沿洹河南北两岸的区域,表明此时人类生产、生活能力有所增强,族邑和聚落选址时,水源的重要性已有所下降。这提醒考古学家在进行聚落考古调查与勘探时,要跳出原有的惯性思维。陶家营、辛店等遗址如同殷墟不同等级的“卫星城”,它们的发现大大突破了传统认知的殷墟范围,也呈现出三级甚至更多的聚落结构形式,这兴许就是甲骨文、金文中的“大邑商”。
但目前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谜,比如辛店遗址这样规模的二级聚落在传统殷墟的外围还有多少?加上三级聚落的中小型遗址,其分布的数量与密度如何?这些不同规模的聚落内结构如何,是单一的族邑聚落,还是如严志斌所称的“工、居、葬合一”模式?
殷墟都邑内部结构研究新思路
已有学者对殷墟都邑的内部结构及发展模式进行研究,只是碍于材料没有重大突破,相关研究也很难有大的突破。但新时代以来,殷墟的一些新发现值得关注。
道路是都城布局的框架,一方面起到沟通连接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不同功能区之间的界线。城市考古中,道路始终是重要遗迹及线索,二里头遗址的“九宫格”式结构形制就是以道路为中心。殷墟很早就发现有道路,但直到2008年在宫殿区以南约1公里发现两条南北向大道、一条东西向连接道,才真正开启以探寻殷墟道路为目标的新方向。此后,在洹河南北两岸均有针对性地进行道路的勘探与发掘,在大司空村、小司空村等地新发现数条道路。其中发现的两条东西向道路与一条南北向道路应有交叉口,两条东西向道路之间南北相距约500米,道路两侧多是夯土居址、灰坑、水井、祭祀坑,甚至是墓葬。联系到殷墟都城有大量不同族邑或工坊,这些由道路区隔出的“街区”是否与不同的族邑或工坊相对应呢?目前尚不能清楚回答,但我们相信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思路,也为今后殷墟勘探与发掘指明了方向。最近新发现的邵家棚遗址,位于殷墟东南部,极有可能是“册”族族邑,多排多进四合院式夯土建筑、墓葬、车马坑等,再现了族邑聚落的内部结构。在今后的勘探与发掘中,一定要高度重视其周边区域是否有大型道路。
因探寻甲骨文的原因,人们最先对殷墟的宫殿区进行考古发掘,但仍有许多待解之谜。池苑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以前对宫殿格局的认识。对“池苑”的了解始于20世纪30年代发掘的“大黄土坑”,2004年—2005年宫殿区重新调查、钻探时,在位于甲组和乙组基址的西侧、丙组基址的西北侧发现池苑。池壁斜陡,中部深12米以上,内填土为黄沙土或淤土,平面呈“倒靴形”,向北与洹河相通,向南伸入宫殿区内,面积不少于4.5万平方米。2018年—2020年再次确认了池苑的范围与结构,面积达6万平方米以上,最深达16米,东侧的宫殿建筑有水沟与之相通。由池苑与洹河围成的“核心岛”及其上的夯土建筑是最重要的发现。目前对于池苑遗存的了解还十分有限,对其形制、年代、性质等都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实际上,相较于宫殿区或其他区域,殷墟王陵区的勘探与发掘工作是最彻底的。尽管历时二百余年,但王陵与祭祀坑布局规整,相互间打破与叠压的关系极少。即便如此,仍存在一个很大的疑问:王陵区的界线在哪里,是否有设施、设备来界定其范围?同样还有连带的问题,即王陵如何与洹河南岸的宫殿交通往来?为了解决上述两大问题,2021年起,对王陵及周边进行了勘探与发掘,并确认了与王陵东西两区对应的两个围沟。东围沟(G1)围绕在大墓和大量祭祀坑周围,东西间距大致为246米,南北236米,沟口宽超过10米,最深3.5米。西围沟(G2)围绕在王陵西区的大墓周围。两个围沟之上各发现缺口两个。多重因素可知,两个围沟与王陵有明确关联。王陵围沟的发现,突破了对陵园布局的原有认知,极大推动了商代陵园制度的研究。
从最初的“兼及四邻”探寻殷墟布局,到如今取得的巨大成就,近百年几代考古人始终有意无意间围绕“何以大邑商”这样的“终极”命题而不懈奋斗,时空维度下动态的殷墟也日渐明朗。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已解决了殷墟布局的所有问题,相反,诸多核心问题尚未解决;而且随着老问题的解决,新问题又不断涌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考古人仍会从时间到空间,从宏观到微观,多维度、多层次、全方面探寻“大邑商”;而以课题制为主导,大规模勘探、小规模发掘,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精细化考古应是解决问题的利器。
(作者:何毓灵,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研究员)
本文为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关键阶段核心聚落综合研究·黄河流域商晚期都邑综合研究》(课题编号:2022YFF0903602)阶段性成果
考古学始终以研究古代遗址的结构与布局为首责,小到水井、房址,大到墓地、作坊,林林总总,都是构成遗址的核心要素。每一位考古学家都曾梦想把所有要素揭示清楚,但往往事与愿违,难以实现。如果加入时间与空间维度,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就更为复杂而持久,很多大型都城遗址都是几代考古人接续努力,才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甲骨文的故乡,商代晚期都城殷墟更是如此。
■百年殷墟考古,试图还原立体的殷墟都城生命史;
■“卫星城”的发现,突破了传统认知的殷墟范围,这兴许就是甲骨文、金文中的“大邑商”;
■发现道路、池苑、围沟,殷墟都邑内部结构探索有了新思路。
“兼及四邻”探索殷墟布局
殷墟甲骨文中,常有“大邑商”“天邑商”“中商”等记载,最早记录“中国”二字的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也明确提到“大邑商”。关于其确切的含义,自甲骨文发现以来,学者们就争议不休,莫衷一是。归纳学者的观点,我们能知晓“大邑商”“天邑商”可以泛指商王朝,也可以确指殷墟都城或王畿地区。但文献看到的多是一个“点”或“面”,无法从多学科、多维度、多视角、全方位深入研究立体的殷墟都城生命史。
自1928年开始发掘以来,厘清殷墟的结构、布局、年代与性质是历代殷墟考古人的主要工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除了宫殿与王陵发掘之外,李济、梁思永等就曾提出“兼及四邻”的思想,积极进行宫殿、王陵之外的探索;1950年后,配合城乡建设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在整个殷墟范围内全面展开,居址、作坊、墓地等不断发现,促使学者们开始思考都邑内部社会结构问题。学者们以殷墟不同阶段的考古新发现、新认识为基础,取得若干研究成果,比如:1979年,杨宝成、杨锡璋通过对殷墟西区近千座墓葬的研究,特别是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指出,殷人“聚族而居、合族而葬”;1995年郑若葵首次探讨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提出“大凡有殷代墓群出现的地方,都可能同时是某一族邑的所在地”。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历时二百余年的殷墟同样如此,它至少经历了初建、兴盛、衰落、废弃等过程。如果把时间维度考虑在内,那么殷墟都邑布局动态变化又会如何呢?2008年岳洪彬等分析更多的殷墟都邑布局元素,在肯定郑若葵提出的族邑模式的基础上指出,殷墟从早期的“点”不断扩展,最终连成“面”,族邑内部(包括宫殿区)具有很多共同的文化要素,如大型取土坑、夯土建筑、墓葬群、作坊、道路、灰坑、窖穴、水井等。2009年唐际根等进一步从聚落考古的角度指出,“洹河流域的商邑至少从规模上呈现明显的一大带众小结构”,在对典型商邑的遗迹构成分类梳理的基础上认为,“大邑商”系由密集分布的诸多小型商邑构成的王都,宫殿与王陵是“大邑商”的核心,道路与水渠是不同族邑的重要连接方式。2022年严志斌指出殷墟“族墓地”存在问题,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严志斌结合殷墟手工业作坊居住、生产与埋葬共存的现象认为,“工、居、葬合一”的工业作坊区模式,是殷墟都城内的主要聚落形态及基层社会组织,工业作坊区在商王族(包括多子族)控制下,以超血缘关系的人群从事手工业生产活动。
从一座都城到三级聚落群
近些年,在传统认知的洹北商城、殷墟区域之外又不断有新的重要考古发现,特别是诸如与洹北商城同时期的陶家营环壕聚落、与殷墟大体同时期的辛店超大型铸铜作坊遗址的发现,又促使大家追问何谓“大邑商”?解答这个世纪难题,还需以考古学为本位。
超大型都邑往往会受到更多的关注,但孤木难成林,都邑之所以能够运转,与相应区域内灿若星辰的中小型聚落是分不开的。采用聚落考古的理念与方法,来解决诸如何谓“大邑商”的问题,仍是有效而重要的手段与途径。宏观角度来讲,作为都邑的殷墟与王畿内外众多族邑、方国的关系问题,既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家治理模式的问题,也是超大型聚落与次级聚落的问题。如果把范围缩小到一个流域,遗址间的相互关系就会更加清晰、直观。洹北商城与殷墟所在的洹河流域曾进行过数次考古调查,其中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美联合调查队进行的调查成果丰硕,洹北商城是此次调查最大的收获。据此,唐际根等提出洹河流域“一大带众小”的布局模式。
2021年发现的陶家营遗址,位于洹北商城以北约4公里,面积近20万平方米。遗址东部围以方形环壕,面积近10万平方米。从勘探与发掘来看,陶家营遗址规模中等,遗址内功能分区较为明确,居址、作坊、墓地等分布井然有序。墓葬之内随葬的大量青铜礼器也表明该遗址的等级不低。这项重要发现,让我们重新审视洹北商城以西约1.4公里的殷墟王陵始建年代,以及洹河南岸20世纪30年代发掘的“小屯五座墓”及“甲组基址”的年代与性质问题。二者也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老大难”问题。
陶家营遗址的发现也让我们转换了思路:与洹北商城470余万平方米庞大的体量相比,商代中期的陶家营与小屯遗址应是洹北商城周边的二级聚落,王陵区78M1墓葬年代表明,王陵始建年代对应洹北商城阶段;安阳县西蒋村遗址等零星的发掘也表明,规模更小的商代中期遗址同样存在;这样就大体形成了洹河流域商代中期三级聚落的社会结构。当然,以后随着考古调查与发掘材料的不断丰富,聚落层次可能会更丰富、更立体。
2016年,在距殷墟宫殿区直线距离10公里处,新发现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辛店遗址,勘探与发掘表明,这里是殷墟目前所知最大的青铜作坊遗址,面积达50万平方米。青铜器铭文表明,从事青铜铸造的家族主要是“戈”族。作坊内部呈现生产、生活与墓葬混杂在一起的布局方式。除辛店遗址外,甚至在传统认知的殷墟分布区的西南、东南等很远的地方,同样发现规模较大、等级不低的晚商时期遗址。这些新发现虽都属洹河流域,但基本远离了历次洹河流域调查时所强调的沿洹河南北两岸的区域,表明此时人类生产、生活能力有所增强,族邑和聚落选址时,水源的重要性已有所下降。这提醒考古学家在进行聚落考古调查与勘探时,要跳出原有的惯性思维。陶家营、辛店等遗址如同殷墟不同等级的“卫星城”,它们的发现大大突破了传统认知的殷墟范围,也呈现出三级甚至更多的聚落结构形式,这兴许就是甲骨文、金文中的“大邑商”。
但目前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谜,比如辛店遗址这样规模的二级聚落在传统殷墟的外围还有多少?加上三级聚落的中小型遗址,其分布的数量与密度如何?这些不同规模的聚落内结构如何,是单一的族邑聚落,还是如严志斌所称的“工、居、葬合一”模式?
殷墟都邑内部结构研究新思路
已有学者对殷墟都邑的内部结构及发展模式进行研究,只是碍于材料没有重大突破,相关研究也很难有大的突破。但新时代以来,殷墟的一些新发现值得关注。
道路是都城布局的框架,一方面起到沟通连接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不同功能区之间的界线。城市考古中,道路始终是重要遗迹及线索,二里头遗址的“九宫格”式结构形制就是以道路为中心。殷墟很早就发现有道路,但直到2008年在宫殿区以南约1公里发现两条南北向大道、一条东西向连接道,才真正开启以探寻殷墟道路为目标的新方向。此后,在洹河南北两岸均有针对性地进行道路的勘探与发掘,在大司空村、小司空村等地新发现数条道路。其中发现的两条东西向道路与一条南北向道路应有交叉口,两条东西向道路之间南北相距约500米,道路两侧多是夯土居址、灰坑、水井、祭祀坑,甚至是墓葬。联系到殷墟都城有大量不同族邑或工坊,这些由道路区隔出的“街区”是否与不同的族邑或工坊相对应呢?目前尚不能清楚回答,但我们相信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思路,也为今后殷墟勘探与发掘指明了方向。最近新发现的邵家棚遗址,位于殷墟东南部,极有可能是“册”族族邑,多排多进四合院式夯土建筑、墓葬、车马坑等,再现了族邑聚落的内部结构。在今后的勘探与发掘中,一定要高度重视其周边区域是否有大型道路。
因探寻甲骨文的原因,人们最先对殷墟的宫殿区进行考古发掘,但仍有许多待解之谜。池苑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以前对宫殿格局的认识。对“池苑”的了解始于20世纪30年代发掘的“大黄土坑”,2004年—2005年宫殿区重新调查、钻探时,在位于甲组和乙组基址的西侧、丙组基址的西北侧发现池苑。池壁斜陡,中部深12米以上,内填土为黄沙土或淤土,平面呈“倒靴形”,向北与洹河相通,向南伸入宫殿区内,面积不少于4.5万平方米。2018年—2020年再次确认了池苑的范围与结构,面积达6万平方米以上,最深达16米,东侧的宫殿建筑有水沟与之相通。由池苑与洹河围成的“核心岛”及其上的夯土建筑是最重要的发现。目前对于池苑遗存的了解还十分有限,对其形制、年代、性质等都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实际上,相较于宫殿区或其他区域,殷墟王陵区的勘探与发掘工作是最彻底的。尽管历时二百余年,但王陵与祭祀坑布局规整,相互间打破与叠压的关系极少。即便如此,仍存在一个很大的疑问:王陵区的界线在哪里,是否有设施、设备来界定其范围?同样还有连带的问题,即王陵如何与洹河南岸的宫殿交通往来?为了解决上述两大问题,2021年起,对王陵及周边进行了勘探与发掘,并确认了与王陵东西两区对应的两个围沟。东围沟(G1)围绕在大墓和大量祭祀坑周围,东西间距大致为246米,南北236米,沟口宽超过10米,最深3.5米。西围沟(G2)围绕在王陵西区的大墓周围。两个围沟之上各发现缺口两个。多重因素可知,两个围沟与王陵有明确关联。王陵围沟的发现,突破了对陵园布局的原有认知,极大推动了商代陵园制度的研究。
从最初的“兼及四邻”探寻殷墟布局,到如今取得的巨大成就,近百年几代考古人始终有意无意间围绕“何以大邑商”这样的“终极”命题而不懈奋斗,时空维度下动态的殷墟也日渐明朗。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已解决了殷墟布局的所有问题,相反,诸多核心问题尚未解决;而且随着老问题的解决,新问题又不断涌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考古人仍会从时间到空间,从宏观到微观,多维度、多层次、全方面探寻“大邑商”;而以课题制为主导,大规模勘探、小规模发掘,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精细化考古应是解决问题的利器。
(作者:何毓灵,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研究员)
本文为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关键阶段核心聚落综合研究·黄河流域商晚期都邑综合研究》(课题编号:2022YFF0903602)阶段性成果
版权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作为参考,不代表本站观点。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果网站中图片和文字侵犯了您的版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处理!转载本站内容,请注明转载网址、作者和出处,避免无谓的侵权纠纷。
下一篇:沈约与钟嵘诗学思想的异同离合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