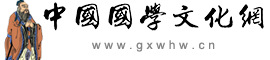栏目: 国学漫谈 作者:佚名 热度:
主持人语
本期主持:郝春文(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 本期主题:古代敦煌民众的社会生活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强调“要加强敦煌学研究”。“敦煌文献等重点古籍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已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敦煌文书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其中保存着丰富的社会生活资料,反映了唐五代宋初敦煌的人口、婚姻、家庭、家族、基层社会组织、教育、民俗、体育和衣食住行等民众生活的诸多方面,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期三篇文章将从结社活动、婚姻礼俗和占卜习俗等方面展示古代敦煌民众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私社是中国古代民众自愿组成的民间团体。这种民间团体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曾广为流行,就活动内容而言,有的从事佛教活动,有的从事经济和生活的互助,更多的私社则同时从事以上两种活动,本文仅以私社的互助活动为例,对其社会功能略作论述。
敦煌私社成员间的互助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丧葬互助。这是最受时人关注的互助活动,在类似章程的“社条”中都有规定。如“敦煌郡等某乙社条一道”(斯5629)规定:“其社人及父母亡没者,吊酒一瓮,人各粟一斗。”“大中年间(公元847至860年)儒风坊西巷社等社条”(斯2041)则规定:“或孝家营葬”,“各助布一疋”,“助粟一斗,饼二拾”,“人各二拾幡”。以上所引“社条”中之“孝家”,就是指社人或其家属亡故的人家。从敦煌私社有关丧葬互助的资料来看,各社规定应缴纳的物品和数量并不一致,一般要缴纳粟、麦、面、饼、油、酒、柴等,有的还需要缴纳布、褐、麻、绫、绢、绣等织物。其中粮食和食物应该是在营葬过程中供丧家及吊唁者食用,白色织物应是用于制作丧服、装殓、盖棺、挽棺之用,彩色织物可能用于制作旌幡等。
二是关于立庄造舍及男女婚嫁的互助。敦煌本“某甲等谨立社条”(伯3730背)规定,社人“若有立庄造舍,男女婚姻,人事少多,亦乃莫绝”。敦煌私社的社条把丧葬互助称为“追凶”或“荣凶”,男女婚嫁造舍等互助则称为“逐吉”。“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正月三日女人社再立条件”(斯527)规定:“社内荣凶逐吉”,“人各油一合,白面一斤,粟一斗”。斯6537背“上祖社条”规定:“社内有当家凶祸,追胸(凶)逐吉”,“人各例赠麦粟等”。从上引社条的规定来看,“逐吉”需要缴纳的物品应该和“追凶”一样,包括粮食、食品和织物等。
三是“赈济急难”,即社人遇到荒年或祸事的互助。“大中年间(公元847至860年)儒风坊西巷社等社条”(斯2041)称:“右上件村邻等众就翟英玉家,结义相和,赈济急难,用防凶变”。并规定:“所置义聚,备拟凶祸,相共助成,益期赈济急难”;“所有急难,各助柴一束”。显然,以上引文中之“凶变”“凶祸”就是对“急难”的定义。“凶变”或“凶祸”当然可以指丧葬,但因前引此社社条对丧葬互助已经另有条款规定,而且以上讨论表明丧葬互助是由社人事发时按规定缴纳助葬物品,而这里的互助物品是从“义聚”中支出。所以,此处的“凶”应该指的是“凶年”,即荒年;“祸”应指社人临时遇到的死亡以外的祸事。斯6537背“十五人结社社条”中有“社众值难逢灾”,这里“难”和“灾”对举,也应该是分别指祸事和自然灾害。而斯6537背“某甲等谨立社条”则称“更有诸家横遭厄难,亦须众力助之”。这里的“横遭厄难”,就是对上文“难”的具体解释。
上文提到“赈济急难”的物品出自私社之“义聚”。“义聚”是私社的公共积累或公共财产,其中的物品有的是社人入社时缴纳的,有的则是私社互助活动的节余。此外,敦煌的私社有严明的纪律,社人违反社条的规定、不听从私社首领的指挥、不参加社邑的活动或未按规定携带物品,都要受到处罚。如伯2556背“社司罚违纪社人记录”载:“没到人张安牛,罚酒半瓮”。另伯36361“社司罚物历”记载马定子等二十多人分别被处以罚粟二斗或一斗的处罚。这些处罚所得物品也被存放在私社的“义聚”中。有材料表明,“赈济急难”还包括在春季青黄不接时借给私社成员粮食种子。如“公元950年前后社司付社人麦粟历”(伯3273)记载私社在春季借给社人马定德等各麦一硕四斗至两硕八斗,粟六斗至一硕二斗。
可见,敦煌私社成员之间的互助几乎涵盖了可造成民众生活发生困穷的所有重要方面。现在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私社的互助力度到底有多大?即能不能真正解决私社成员遭遇的困难?以下以丧葬互助为例略作说明。
唐俗重厚葬,所费往往超出民户的负担能力,是导致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唐穆宗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十二月李德裕奏:“缘百姓厚葬,及于道路,盛设祭奠,兼置音乐等。闾里编氓,罕知报义,生无孝养可记,殁以厚葬相矜。或结社相资,或息利自办,生业以之皆空。习以为常,不敢自废。人户贫破,抑此之由”(《唐会要》)。这里也把“结社相资”看作解决厚葬所需物品的途径之一。从敦煌社邑文书中有关丧葬互助的材料来看,由于社人贫富不同,各社成员多寡不同,社人在遇到丧葬时获得的助葬物品是有差异的。如“辛未年(公元971年)三月八日沈家纳赠历”(伯4975)收到社人助葬的各种绫九十八丈九尺、各种绢二十丈二尺、黄画被子一丈四尺,共计一百二十丈五尺,连同主人拿出的绢、锦、绫等十余丈,约当唐前期六十余丁之调。因为此私社由县令、兵马使、押衙等敦煌地区上层和富户组成,所以收到的助葬品较为丰厚。而“辛酉年(公元961年)十一月廿日张友子新妇身故聚赠历”(斯4472背)全社五十人,所纳赠的各种褐布一百零一丈,约当唐前期四十丁之调。这个是由普通民众组成的社,收到的助葬物品也不算少。至于纳赠的粮食和食物,数量也很大。如“丙子年(公元976年)四月十七日祝定德阿婆身故纳赠历”(斯1845)用粟六石,饼一千枚。“辛酉年(公元961年)十一月廿日张友子新妇身故聚赠历”(斯4472背),则是交付丧家饼八百四十枚,粟三石四斗,油三十合,柴三十三束。“辛巳年(公元981年)十月廿八日荣指挥葬巷社纳赠历”(斯2472背)则是交付丧家油三十一合,饼五百六十枚,粟两石,柴三十一束。这样大的数量,不仅一般民户无力承担,就是中产之家、中下级官吏恐怕亦感吃力。可见,“结社相资”的确可以帮助社人渡过丧葬难关。其他互助活动对社人的救济作用由此不难想见。
小农和小手工业者是很脆弱的个体经济,风调雨顺的正常年景,多数也只是在温饱线挣扎,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遭遇天灾人祸,很容易进入“贫破”者队伍。唐五代宋初敦煌私社的互助活动,实际上给这些小生产者提供了免于“贫破”的保障,使他们可以安然渡过如丧葬、荒年、造舍、男婚女嫁以及突发的厄难等一系列人生的难关。通过互助,贫弱者可以维持简单再生产,殷实者可以实现扩大再生产。由于以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为代表的小生产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体,也是支撑唐五代社会的基石,所以,社邑的互助活动不仅仅有益于参加社邑的个体,同时有益于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正常年景下,总会有一些小生产者因各种缘由破产,也总会有另外一些小生产者可以实现扩大再生产。但如果某一时期破产者过多,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再生产,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有可能造成社会动乱和动荡。唐五代宋初敦煌私社的互助活动不仅可以大大降低小生产者破产的数量,同时有助于增加扩大再生产群体的数量,其结果是既有利于整个社会维持简单再生产,也有利于扩大社会再生产。因而具有维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
还应该指出,结社互助不是敦煌地区特有的现象。前引李德裕奏中也提到了“结社相资”。而韦挺在唐太宗时所上《论风俗失礼表》中也曾说:“又闾里细人,每有重丧,不即发问,先造邑社,待营办具,乃始发哀。至假车乘,雇棺椁,以荣送葬。既葬,邻伍会集,相与酣醉,名曰出孝”(《全唐文》)。唐代诗人王梵志则有更为形象的描绘:“遥看世间人,村坊安社邑。一家有死生,合村相就泣”(《王梵志诗》)。这说明在唐五代宋初的中原地区,也广泛流行结社互助现象。此外,在敦煌以西的西州(今吐鲁番),也发现了结社互助的材料,甚至在黑水城文书中还发现了西夏文结社互助的材料,说明结社互助活动在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也曾流行。但如果不是敦煌社邑文书的发现,在传世文献和各地的零星资料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也难以进行深入的讨论。所以,对敦煌社邑文书的深入研究不仅加深了对敦煌地区社邑情况的具体了解,也大大深化了对唐五代时期全国社邑发展情况的认识。
(作者:郝春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
本期主持:郝春文(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 本期主题:古代敦煌民众的社会生活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强调“要加强敦煌学研究”。“敦煌文献等重点古籍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已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敦煌文书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其中保存着丰富的社会生活资料,反映了唐五代宋初敦煌的人口、婚姻、家庭、家族、基层社会组织、教育、民俗、体育和衣食住行等民众生活的诸多方面,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期三篇文章将从结社活动、婚姻礼俗和占卜习俗等方面展示古代敦煌民众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私社是中国古代民众自愿组成的民间团体。这种民间团体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曾广为流行,就活动内容而言,有的从事佛教活动,有的从事经济和生活的互助,更多的私社则同时从事以上两种活动,本文仅以私社的互助活动为例,对其社会功能略作论述。
敦煌私社成员间的互助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丧葬互助。这是最受时人关注的互助活动,在类似章程的“社条”中都有规定。如“敦煌郡等某乙社条一道”(斯5629)规定:“其社人及父母亡没者,吊酒一瓮,人各粟一斗。”“大中年间(公元847至860年)儒风坊西巷社等社条”(斯2041)则规定:“或孝家营葬”,“各助布一疋”,“助粟一斗,饼二拾”,“人各二拾幡”。以上所引“社条”中之“孝家”,就是指社人或其家属亡故的人家。从敦煌私社有关丧葬互助的资料来看,各社规定应缴纳的物品和数量并不一致,一般要缴纳粟、麦、面、饼、油、酒、柴等,有的还需要缴纳布、褐、麻、绫、绢、绣等织物。其中粮食和食物应该是在营葬过程中供丧家及吊唁者食用,白色织物应是用于制作丧服、装殓、盖棺、挽棺之用,彩色织物可能用于制作旌幡等。
二是关于立庄造舍及男女婚嫁的互助。敦煌本“某甲等谨立社条”(伯3730背)规定,社人“若有立庄造舍,男女婚姻,人事少多,亦乃莫绝”。敦煌私社的社条把丧葬互助称为“追凶”或“荣凶”,男女婚嫁造舍等互助则称为“逐吉”。“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正月三日女人社再立条件”(斯527)规定:“社内荣凶逐吉”,“人各油一合,白面一斤,粟一斗”。斯6537背“上祖社条”规定:“社内有当家凶祸,追胸(凶)逐吉”,“人各例赠麦粟等”。从上引社条的规定来看,“逐吉”需要缴纳的物品应该和“追凶”一样,包括粮食、食品和织物等。
三是“赈济急难”,即社人遇到荒年或祸事的互助。“大中年间(公元847至860年)儒风坊西巷社等社条”(斯2041)称:“右上件村邻等众就翟英玉家,结义相和,赈济急难,用防凶变”。并规定:“所置义聚,备拟凶祸,相共助成,益期赈济急难”;“所有急难,各助柴一束”。显然,以上引文中之“凶变”“凶祸”就是对“急难”的定义。“凶变”或“凶祸”当然可以指丧葬,但因前引此社社条对丧葬互助已经另有条款规定,而且以上讨论表明丧葬互助是由社人事发时按规定缴纳助葬物品,而这里的互助物品是从“义聚”中支出。所以,此处的“凶”应该指的是“凶年”,即荒年;“祸”应指社人临时遇到的死亡以外的祸事。斯6537背“十五人结社社条”中有“社众值难逢灾”,这里“难”和“灾”对举,也应该是分别指祸事和自然灾害。而斯6537背“某甲等谨立社条”则称“更有诸家横遭厄难,亦须众力助之”。这里的“横遭厄难”,就是对上文“难”的具体解释。
上文提到“赈济急难”的物品出自私社之“义聚”。“义聚”是私社的公共积累或公共财产,其中的物品有的是社人入社时缴纳的,有的则是私社互助活动的节余。此外,敦煌的私社有严明的纪律,社人违反社条的规定、不听从私社首领的指挥、不参加社邑的活动或未按规定携带物品,都要受到处罚。如伯2556背“社司罚违纪社人记录”载:“没到人张安牛,罚酒半瓮”。另伯36361“社司罚物历”记载马定子等二十多人分别被处以罚粟二斗或一斗的处罚。这些处罚所得物品也被存放在私社的“义聚”中。有材料表明,“赈济急难”还包括在春季青黄不接时借给私社成员粮食种子。如“公元950年前后社司付社人麦粟历”(伯3273)记载私社在春季借给社人马定德等各麦一硕四斗至两硕八斗,粟六斗至一硕二斗。
可见,敦煌私社成员之间的互助几乎涵盖了可造成民众生活发生困穷的所有重要方面。现在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私社的互助力度到底有多大?即能不能真正解决私社成员遭遇的困难?以下以丧葬互助为例略作说明。
唐俗重厚葬,所费往往超出民户的负担能力,是导致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唐穆宗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十二月李德裕奏:“缘百姓厚葬,及于道路,盛设祭奠,兼置音乐等。闾里编氓,罕知报义,生无孝养可记,殁以厚葬相矜。或结社相资,或息利自办,生业以之皆空。习以为常,不敢自废。人户贫破,抑此之由”(《唐会要》)。这里也把“结社相资”看作解决厚葬所需物品的途径之一。从敦煌社邑文书中有关丧葬互助的材料来看,由于社人贫富不同,各社成员多寡不同,社人在遇到丧葬时获得的助葬物品是有差异的。如“辛未年(公元971年)三月八日沈家纳赠历”(伯4975)收到社人助葬的各种绫九十八丈九尺、各种绢二十丈二尺、黄画被子一丈四尺,共计一百二十丈五尺,连同主人拿出的绢、锦、绫等十余丈,约当唐前期六十余丁之调。因为此私社由县令、兵马使、押衙等敦煌地区上层和富户组成,所以收到的助葬品较为丰厚。而“辛酉年(公元961年)十一月廿日张友子新妇身故聚赠历”(斯4472背)全社五十人,所纳赠的各种褐布一百零一丈,约当唐前期四十丁之调。这个是由普通民众组成的社,收到的助葬物品也不算少。至于纳赠的粮食和食物,数量也很大。如“丙子年(公元976年)四月十七日祝定德阿婆身故纳赠历”(斯1845)用粟六石,饼一千枚。“辛酉年(公元961年)十一月廿日张友子新妇身故聚赠历”(斯4472背),则是交付丧家饼八百四十枚,粟三石四斗,油三十合,柴三十三束。“辛巳年(公元981年)十月廿八日荣指挥葬巷社纳赠历”(斯2472背)则是交付丧家油三十一合,饼五百六十枚,粟两石,柴三十一束。这样大的数量,不仅一般民户无力承担,就是中产之家、中下级官吏恐怕亦感吃力。可见,“结社相资”的确可以帮助社人渡过丧葬难关。其他互助活动对社人的救济作用由此不难想见。
小农和小手工业者是很脆弱的个体经济,风调雨顺的正常年景,多数也只是在温饱线挣扎,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遭遇天灾人祸,很容易进入“贫破”者队伍。唐五代宋初敦煌私社的互助活动,实际上给这些小生产者提供了免于“贫破”的保障,使他们可以安然渡过如丧葬、荒年、造舍、男婚女嫁以及突发的厄难等一系列人生的难关。通过互助,贫弱者可以维持简单再生产,殷实者可以实现扩大再生产。由于以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为代表的小生产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体,也是支撑唐五代社会的基石,所以,社邑的互助活动不仅仅有益于参加社邑的个体,同时有益于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正常年景下,总会有一些小生产者因各种缘由破产,也总会有另外一些小生产者可以实现扩大再生产。但如果某一时期破产者过多,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再生产,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有可能造成社会动乱和动荡。唐五代宋初敦煌私社的互助活动不仅可以大大降低小生产者破产的数量,同时有助于增加扩大再生产群体的数量,其结果是既有利于整个社会维持简单再生产,也有利于扩大社会再生产。因而具有维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
还应该指出,结社互助不是敦煌地区特有的现象。前引李德裕奏中也提到了“结社相资”。而韦挺在唐太宗时所上《论风俗失礼表》中也曾说:“又闾里细人,每有重丧,不即发问,先造邑社,待营办具,乃始发哀。至假车乘,雇棺椁,以荣送葬。既葬,邻伍会集,相与酣醉,名曰出孝”(《全唐文》)。唐代诗人王梵志则有更为形象的描绘:“遥看世间人,村坊安社邑。一家有死生,合村相就泣”(《王梵志诗》)。这说明在唐五代宋初的中原地区,也广泛流行结社互助现象。此外,在敦煌以西的西州(今吐鲁番),也发现了结社互助的材料,甚至在黑水城文书中还发现了西夏文结社互助的材料,说明结社互助活动在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也曾流行。但如果不是敦煌社邑文书的发现,在传世文献和各地的零星资料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也难以进行深入的讨论。所以,对敦煌社邑文书的深入研究不仅加深了对敦煌地区社邑情况的具体了解,也大大深化了对唐五代时期全国社邑发展情况的认识。
(作者:郝春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
版权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作为参考,不代表本站观点。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果网站中图片和文字侵犯了您的版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处理!转载本站内容,请注明转载网址、作者和出处,避免无谓的侵权纠纷。
相关推荐